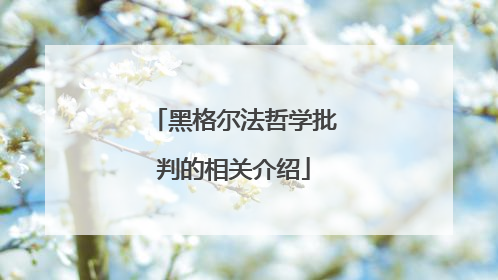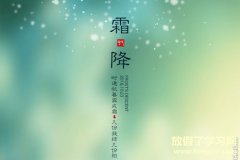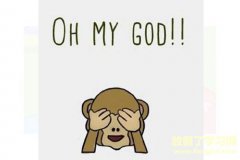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jh 叔本华说黑格尔哲学是“赤裸裸的胡说、拼凑空话无意义的疯狂的词组”,是“只有在疯人院里听到过的最大的狂妄”……额~叔本华和黑格尔的发型都很酷 无处不哲学编辑 / 戴文麟 / 著 摘要: 叔本华是现代西方最早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哲学家之一。他站在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批评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错误”态度,指出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是“完全虚构”,是变相的神学,是为普鲁士政府服务的哲学。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既包含合理成份,也存在一些错误。这一批判推动了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变。 向理性主义哲学权威的挑战 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叔本华是现代西方最早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哲学家之一。早在19世纪20年代,当黑格尔哲学处于顶峰状态、黑格尔本人的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叔本华就敢于藐视权威挺身而出公开向黑格尔哲学发起挑战。他在柏林大学的课堂上与黑格尔对垒,谴责黑格尔等哲学家是“诡辩家”,“他们用野蛮神秘的语言使时代的思想力量疲倦”,“使大家失掉哲学的信仰”,并大声疾呼应该取消他们的“哲学家资格”,“像古时一样,牟利的人都要赶出庙宇”。除此之外,叔本华更多的是在其著作中不断地对黑格尔进行激烈的攻击。他丑化黑格尔哲学是“赤裸裸的胡说、拼凑空话无意义的疯狂的词组”,是“只有在疯人院里听到过的最大的狂妄”;斥骂黑格尔是“最厚颜无耻的”、“臭名昭著的骗子”;还将他比作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丑鬼,称他是“精神上的咖利本”。其言词之尖刻为思想史上罕见。叔本华所以对黑格尔及其哲学采取如此仇恨的态度,根本缘由在于他的哲学思想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尖锐对立,他坚决反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下面我们将着重论述叔本华如何在理论上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 一 叔本华与黑格尔在哲学观点上的对立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康德哲学的态度上。 康德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康德哲学博大精深,但也包含众多矛盾。它是一种二元论哲学。它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作为感觉源泉的客观的物自体,和根据先验认识形式整理感觉而形成的主观现象,它认为人的认识只能达于现象而不能达到物自体。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为从它出发的后世哲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 黑格尔哲学渊源于康德哲学。黑格尔高度评价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并加以继承,同时又对康德哲学进行批判。批判的重点是关于物自体的学说。黑格尔指责康德“自谦不能认识物自体的批判主义”为“缺乏深思”的一种“浅薄作风”。在他看来,康德所说的那种独立于意识之外、不可知的物自体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实际是“一个极端抽象、完全空虚的东西”,“不过只是思维的产物,只是空虚的自我或不断趋向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既然如此,物自体就没有超出思维、自我之外,就不是不可知的,甚或可以说“再没有比物自体更容易知道的东西了”。其次,与康德关于现象与本质(作为物自体)绝然对立、通过现象不能认识本质的观点相反,黑格尔认为本质与现象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本质性在现象中出现,所以,现象不单纯是没有本质的东西,而是本质的显现”。“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同时即认识了本质”。可以看出,黑格尔对于康德物自体学说的批判,是要清除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不可知论,以建立其以理性为基础的绝对唯心主义同一哲学。 叔本华哲学同样渊源于康德哲学。叔本华公开声明他的哲学“是从康德哲学出发的”。但是,他对于康德物自体学说的态度却不同于黑格尔。他称赞“康德的最大功绩是划清现象与自在之物(两者之间)的区别”。他接受了康德把世界二分化为现象与物自体的观点,承认在现象之外存在着理性认识所不可及的物自体,并将这一观点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 叔本华之所以对康德的物自体学说采取上述态度,是因为在他看来,按照康德的这一学说,现象是由认识主体所构成的,因而说明它是虚幻的,相反只有理性所达不到的物自体才是真正的实在。这一学说揭示了理性的局限,以及单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现象界的虚妄,告诉人们要对虚幻的现象界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理性所蒙骗,努力去寻求现象背后真正的实在。 叔本华根据自己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对于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态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责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没有能力来评价康德的伟大的功绩”,他们对康德哲学的了解“不过是一些凤毛麟角以及纯粹的外表”,他们“误解了康德的体系”,他们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胡扯”,“没有能够有力地反驳”,只是“笨拙而粗鲁地攻击”,“就像是野蛮人在向他们所不熟悉的希腊神像掷石头”。叔本华告诫德国青年千万不要通过黑格尔的著作去学习康德哲学,那样只会使他们“扭伤了、损坏了头脑”,而不能“追随康德那种意味深长的探讨”。 叔本华对黑格尔的上述批评有许多是违背事实的。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态度并不是像叔本华所批评的那样。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既有批判,也有继承。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主张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的同一,在哲学发展史上是有功绩的,叔本华对此却全盘否定,这是错误的。而叔本华本人对康德哲学的态度也包含着错误。他肯定康德的自在之物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是为了给理性加以限制,为他确立非理性的意志这一精神性的自在之物奠立理论基础。但是,由于黑格尔所主张的是以思维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叔本华为了肯定自在之物,批评这种同一学说的虚妄,深刻地揭露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错误本质,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 叔本华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前者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后者是理性主义哲学,叔本华站在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批判。 理性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理性占有绝对统治地位,“除了理性外更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理性是绝对的力量”。黑格尔所说的理性不仅指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也即“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在人和自然界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而世界不过是理性的外化。但是,他又指出,理性外化为世界要经历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理性自我实现、同时又是它自我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理性以纯概念的形式自我发展,第二阶段理性外化为自然,第三阶段理性又通过人的精神自我认识,回复到自身。对于理性这三个阶段辩证运动的论述,分别构成了无所不包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黑格尔的这套理性主义哲学,对于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来说不啻是一个神话,他根本无法理解。叔本华对于理性自有他的另一套看法。在叔本华看来,人的认识不过是由非理性的意志所派生、并为它服务的工具。他将人对表象世界的认识分为两种:直观认识和理性认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理性的功能只是在直观的基础上“构成概念”。概念是一般,它是直观的复写,它的内容全部来自直观,是对于同类直观认识共同属性的概括。根据上述两种认识产生的过程,叔本华指出,只有直观才是“真理的源泉”,而理性的作用只是保存知识、传达知识、运用知识。 叔本华根据自己对理性的看法来审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他认为后者完全歪曲了理性,是“在一种完全虚构的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叔本华看来,概念既是个别认识的普遍概括,其内容应少于个别认识,并且概念愈抽象、普遍,其内容愈少,据此,黑格尔哲学中那个最高、最一般的绝对观念其内容应是“最为空洞的和最为贫乏的,最后成了纯粹的外壳”。但黑格却将这个绝对观念看作具有无限内容、包含一切、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绝对,叔本华指出这样一个“不受条件限制的{绝对}简直是不存在的怪物”,他嘲笑黑格尔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个怪物的存在根本无法证明,他们只能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声嘶力竭地叫喊、虚张声势地吓人:“绝对,该死的!它必须存在,否则一切都将不存在!”“绝对是从哪里来的?‘多么愚蠢的问题!难道我没有告诉你它是绝对吗’。” 其次,这个绝对观念又是如何创造出世界呢?叔本华指出,黑格尔哲学是“把宇宙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演绎法,从绝对中推演出来”,而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而也是错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叔本华认为认识主体理性与客体认识对象(世界万物)二者相互联系,互为存在的前提,“与客体同时,主体已立即同在,相反亦然”,在它们之间,“既不能在客体对主体、也不能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上安置从后果到原因这一关系”,不能说一方作为原因产生另一方。黑格尔哲学的错误恰恰在于不懂这一道理,误将理性作为客体产生的原因。 第二,叔本华指出黑格尔所论述的绝对观念演绎世界的过程是对于人类正常认识过程的颠倒。在人的认识中,概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而产生的,但黑格尔哲学“不但不将概念认作从事物抽象来的思想,反而使概念成为原始的东西而在事物中只看到具体的概念”,这是将“颠倒了的世界作为哲学上的一出丑剧搬到墟场上上演”;是“把一个普通的理智——大自然的单纯制品——当作掌管人类精神、奇迹和圣物的东西而呈现给了判断力尚未成熟的、最诚实而又易于轻信的年轻人”。 叔本华还将黑格尔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进行比较,指出它们的哲学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黑格尔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宗教神学,它的全部内容就是为下列宗教信条“提供一个哲学基础”:“存在着一个上帝、造物主和宇宙的统治者,一个被赋予知性和意志的人格的,因而也就是单个人的存在,她从虚无中创造出了世界,并且用她那崇高的智慧力量和仁慈统治这个世界”。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观念实际上扮演了基督教中上帝的角色。根据上述状况,叔本华把黑格尔哲学称作“故弄玄虚的神秘主义”,说它是经院哲学的“单纯的模仿”,是“应当能代表基督教的一种怪物”,“而且和经院哲学一样注定是为神学服务的。 应当说叔本华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错误的分析,以及对其宗教唯心主义本质的揭露,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要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叔本华的批判与后来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有某些相似之处,尽管两人批判的立场并不一样。费尔巴哈在分析黑格尔哲学的错误时也曾指出:“思辨哲学的绝对或无限,……不过是不加规定的、不确定的东西——抽去一切规定的抽象”。“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他还揭露,“黑格尔关于自然、实在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等等。但须指出的是,叔本华提出类似于上述的判断却要早于费尔巴哈数十年。 三 叔本华在分析黑格尔哲学错误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揭露了它在当时德国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在19世纪的德国,黑格尔哲学统治了当时整个思想教育界,叔本华带着愤懑的情绪描述了这一情景。他写道:“现在已经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当然不得不献身于研究‘黑格尔伟大的精神’”,他们“用全付精力对这些庸才无休止的平淡无奇的作品进行枯燥的研究,滥用分配给他们短暂的、极为宝贵的大好时光,而没有用这样的时光去获得……那些极为稀少的、名符其实的、真正罕见的思想家的??…可靠知识”。 叔本华认为让学生们耗费大量宝贵的时光去研究“荒唐”的黑格尔哲学,不仅“毒害”了他们的思想,而且带坏了整个一代人的学风。他指出,当时德国学术界缺乏严肃认真的研究空气,既不认真研究前人伟大的哲学思想,也不认真研究现代科学知识,但是“每一个初学者都可以对一些曾经使最伟大的思想家大伤脑筋的问题随便发表意见”。一些庸俗之辈拙劣地模仿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唱起哲学的高调,把宇宙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演绎法,从绝对中推演出来,这种推演一个比一个更令人厌烦”。 把黑格尔哲学对于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全部说成是坏的,这是十分片面的,我们在后面将对此进行论述。但是,应当承认叔本华在这里所列举的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当时德国文化学术界所产生的一些不良现象确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有同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牛皮理论家杜林喜好模仿黑格尔从绝对出发构造体系一事,指出这种现象在当时德国的普遍性:“……‘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叔本华对这种现象的揭露,在相当程度上是切中时弊的。黑格尔哲学在德国为什么能造成那么大的声势,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叔本华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普鲁士政府对它的大力支持。普鲁士政府和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叔本华对这一关系中的两方都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学者们是抱着个人名利的目的来从事哲学研究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地用自己的哲学来为普鲁士政府服务。“他们的哲学感召是来自官府”。他们每提出一个哲学观点都要考虑“政府的意向、国教的规程、出版人的愿望、同事们良好的友谊、当时的政治倾向、公众一时的风尚等等”因素。而普鲁士政府作为回报便对黑格尔哲学大力扶持。该学派的哲学家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丰厚的报酬和煊赫的地位,他们的哲学被大肆吹捧和宣扬,叔本华称黑格尔哲学是“以工资俸禄、甚至是以宫廷顾问头衔配备起来的哲学”。他不无气愤地责问道:“有哪一个时代像德国近二十年来那样对一种坏透了的东西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吹捧?有哪一个时代有过这样将无意义的和荒谬可笑的东西尊奉为类似神明的?”在他看来,普鲁士政府的所作所为和黑格尔哲学的辉煌地位确实证明了,“用大笔的钱就可以把一个最坏的权欲狂和一个最坏的哲学家拥上宝座”。 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与普鲁士政府关系的分析是极其尖刻的,其中包括一些过激之词。为什么叔本华会作如此激烈的批评?也许与他一个时期受到政府的冷遇,妒忌黑格尔哲学得到恩宠有关,但不论怎样,他指出黑格尔哲学自觉地为普鲁士政府服务,因而受到后者的青睐,这一分析是基本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黑格尔哲学时也经常谈到这一方面的情况。例如,恩格斯在分析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时就指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黑格尔和歌德一样,“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庸人的气味”。 四 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存在很多缺陷、错误,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 首先,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是片面的。我们知道,尽管黑格尔哲学是一种错误的唯心主义哲学,但它内部包含着巨大的精神财富。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哲学时正确地指出,“……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如果人们不是停留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脚手架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在这些珍宝中最具有价值的就是它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即“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这是黑格尔对人类思想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叔本华无视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财富,对辩证法一窍不通。他在其著作中很少谈到辩证法,偶而谈到也只是将它当作“逻辑学的同义词”;认为它仅是一种“争辩的技能”或“精神格斗的技能”。更有甚者,他还将全部黑格尔哲学贬为“胡说八道”、“瞎吹牛”、“令人作呕的废话”。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严重歪曲,这种歪曲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叔本华的无知和他顽固地坚持非理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 其次,叔本华虽然在理论上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总的说来,正如俄国学者贝霍夫斯基所说:“叔本华多半不是同他们(指德国古典哲学著名代表)争论,不是对他们学说作有根据的批驳,而是满腔愤恨地指责和痛骂他们。不仅在现在,就是在叔本华生前,他的这种粗暴态度也为当时的人所不满。丹麦皇家科学院就为这一原因而拒绝给当年该院科学奖唯一的申报者、叔本华的著作《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授奖,批评在该书中“好几个近代哲学家被不得体地提到,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恼怒和不快”。 叔本华的批判不仅是粗暴的,而且有些批判是“无中生有”,硬将原不是黑格尔的、甚至是他所反对的观点加到他头上。例如,叔本华批评黑格尔所以主张取消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是因为他虚构了理性有一种神秘的认识形而上学本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天生地存在于我们之中”,它是“一种‘超感觉的’能力,或者说一种‘理念’的能力”,是“对于绝对的直接的直觉”,并指出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来自耶可比。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诬陷”。黑格尔从未赞成过耶可比的直觉理论,而是一贯反对。黑格尔认为,一切认识都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纯粹的、无需中介的直接认识(即直觉)不可能获得真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叔本华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唯物主义。在叔本华看来,唯物主义也是一种错误的哲学,唯物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犯了同样的错误,它也不懂得主客体二者是互相联系、互为存在前提的,主体既不能独立于客体并产生客体,客体也不能独立于主体并产生主体。“须知‘没有一个客体无主体’就是使一切唯物论永不可能的一条定律。”由于唯物主义与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叔本华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流行也助长了唯物主义的传播:“当今一代学者的头脑被黑格尔的胡说搅乱了:他们不会反思,既粗俗又胡涂,完全沦为一种从蛇妖的蛋里爬出来的浅薄的唯物主义的牺牲品。”“……早就埋伏在那里的唯物主义便昂起头来,与它的伙伴、有时也称作人道主义的兽道主义手挽着手大出风头。”叔本华在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他对于这一哲学特别痛恨,他在写给弗劳恩施塔的信中表示了对这个“被人们供上神几的复活了的德谟克里特”的忿恨之情。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实际是“一箭双雕”:既射中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又射中唯物主义。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建立他自己的、其错误荒谬不下于黑格尔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扫清道路。 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已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并未能建立起符合理性主义原则的公正合理的社会,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却充满各种矛盾和危机,在残酷的现实的面前,理性主义哲学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它在理论上的缺陷也愈益暴露,这种情况表明,原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已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继续存在下去了。资产阶级需要新的哲学。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的需要。因此,尽管这一批判存在着各种缺陷、错误,尽管叔本华所要建立的非理性主义的意志主义哲学也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但叔本华在哲学理论方面所作的一切毕竟代表了未来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促进了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化。叔本华在黑格尔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敢于最先向它提出挑战,这种藐视权威的理论勇气是值得赞扬的。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以及其意志主义哲学的创立,使他在1848年后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名声大振,确立了他作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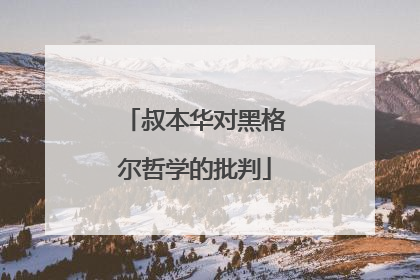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简介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一本早期著作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1843年夏天写于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故又称《克罗茨纳赫手稿》。原稿共39张,没有标题,现标题是1927年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表这一手稿时加的。中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这部著作是对G.W.F.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第261~313节阐述国家问题的部分所作的分析和批判。 马克思在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通过参加现实斗争,动摇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退出《莱茵报》后,他系统地研究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阅读了L.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得到很大启发,于是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但是,和费尔巴哈只注重自然和宗教批判不同,马克思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把被他颠倒了的逻辑观念和现实事物的关系颠倒过来,指出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批判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的观点,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著名结论;批判了黑格尔主张君主、官僚决定国家制度的英雄史观,阐明了人民创造国家的思想;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发展问题上否认有质变的缓慢进化论,提出必须经过真正的革命来建立新国家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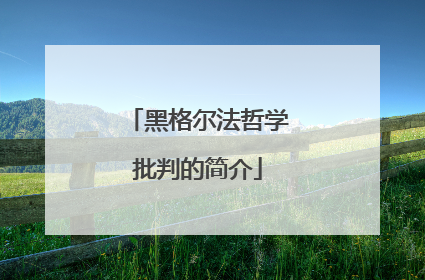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介绍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一本早期著作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1843年夏天写于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故又称《克罗茨纳赫手稿》。原稿共39张,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1927年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表这一手稿时加的。

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如何理解
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经由最初的康德主义走向黑格尔主义,继而转变为新理性批判主义,最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中趋于成熟,并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中,他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观出发并且充分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精华,对黑格尔的理性法思想提出了挑战:通过对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关系的阐述和对于私有制的抽象——长子继承制的分析,得出了与黑格尔相反的结论,即: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相关介绍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追随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后来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念来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费尔巴哈从宗教问题出发,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人的本质就是人自身。宗教的产生是人性异化的后果。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由此批判人的异化。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异化的社会原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苦难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宗教中的苦难就是现实世界中苦难的歪曲的反应。要批判宗教,最彻底的做法是彻底的推翻颠倒的社会关系,推翻异化人性的社会制度。颠倒的现实世界一旦被推翻,宗教幻想的天国也就随之瓦解了。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又对当时处在封建复辟状态的德意志各邦的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出,正如15世纪的宗教改革是在僧侣头脑中发端的一样,当前德意志的政治改革应该是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发端的。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和揭露,以便唤醒德意志的政治革命,但“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只有通过革命斗争而不是哲学上的辩论,才能促进德国政治的演进。在革命的力量上,马克思注意到了当时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的作用,提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于“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无产阶级。因为“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中,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有以下几点:人的本质归根结底并不仅仅是宗教的本质这种抽象物,更不是脱离社会的孤立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主观的实践是必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的能动性思维能通过实践作用于客观;要用哲学改变世界,必须把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考量------“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总之,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得不留情面,是因为他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大多数哲学家们不停的编造新词汇解释世界,与其妥协,只是在意识形态上打转,也就是说,只是要改变关于世界的观念,而无法改变世界本身。在从思想的天国下降到现实生活方面------即在现实中实现哲学继而消灭哲学方面,大多数哲学家都没有触及,这使得哲学的作用多数时候只停留在思维上,而没有切入实际,从而不具有物质力量。但是在历史进程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是关键的。马克思认为,由于人不是孤立抽象的人,而是与所处环境联系在一起,所以人有充分的动机去改变环境,而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只要彻底,“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费尔巴哈等哲学家却在涉及人时陷入了唯心主义,将人周围的世界抽象化了,抽离了,苦难变成了非普遍现象,变成了少数人的例外,而与社会现实无关,所以费尔巴哈等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或是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为现实”,总之他们忽略了有主观的实践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所以马克思在剖析德国现状时痛心地说道,“在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内容,精神生活也同实践缺乏联系。”可以说,马克思激烈批判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他认为他们的观点的缺陷正是当前德国最致命的缺陷,因为“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的产生,看来既没有任何前提,也没有必要的基础”(毫无疑问,要产生“彻底需要”,必须使人和所处社会环境紧密相联)。这个缺陷导致“(法国和英国)那里,正在解决问题;(德国)这里,矛盾才被提出”,“德国并不是和现代各国同一个时候登上解放的阶梯,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还没有达到”,“(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也就是说,德国的实践和精神不仅相互脱离,而且实践水平大大低于英法等国家。德国落在了后面。当然马克思并不会认为是某些哲学家们导致了德国的此种畸形的意识形态,但他认为他们至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极大的影响了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大声疾呼:“应该像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而过去的回音依然压抑着这些国家……德国人的解放就使人的解放…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同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费尔巴哈》中,都用了不少篇幅来彻底批判宗教。因为他认为,既然宗教是这个现实的,不合理的,“颠倒了的”世界的产物,是为其服务的有感情的制度,是其“总的理论”,那么对宗教的批判的预期的目标便是批判那个“颠倒了的世界”本身,是批判使宗教产生的社会矛盾本身。虽然说在“人创造了宗教”这一基本点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是一致的,但马克思显然认为这不足以使费尔巴哈的观点免于被批判。因为尽管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人的本质,但他把人的本质抽象孤立地看待,他被遮蔽,从而不可能看到最根本的现实性的问题------宗教的产生是由于历史进程,宗教里所表现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以及寻求慰藉,宗教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因为现实的普遍的社会矛盾,而不是因为个别人的偶然,而且,宗教这种作为“颠倒了的”世界的总理论的意识,也绝对不是单个的人所能产生的,它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中。费尔巴哈的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了,但却没有要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意思,因为他的精神与实践脱节,由于没有和实践结合,它的观点缺乏更实际的意义,根本无法切入现实,从而对现实作些改变。而马克思认为,要消灭宗教最根本的原因和最大的意义就是,一个不需要宗教来麻醉的世界才是真正合理的,幸福的。因此宗教批判不仅要使人摆脱对自己处境的幻想,还要使人作为有理性的人真正来思想和行动,来使宗教批判真正实现其最大意义-----改变使人抗议的现实,来建立自己所需要的现实性,“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反复强调的观点就在于此,他希望德国不再止于思维,而是跨出实践的步伐,去尝试发掘思想的更大更现实的效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法律思想在这部写于1843年7、8月间的篇幅巨大的未完成的手稿中,马克思不仅用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地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法哲学本体论,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著名论断,还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法学辩证法思想,提出了在矛盾分析基础上“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唯物主义法学辩证法观,进而在法学本体论和法学方法论两个方面突破了黑格尔,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法律观向唯物主义法律观转变的重要标志。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一)、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法学观,明确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黑格尔完全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把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当作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而把社会的经济关系当作派生的东西。在他那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颠倒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不是国家及其“理念”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页)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它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这样,马克思就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法的“主词”与法的“宾词”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确定了从市民社会到国家和法的唯物主义法哲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说明了财产关系与法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就是财产,揭示了法与财产关系的本质联系:法是财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财产关系则是法的实在内容。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的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他还进一步深入剖析了“长子继承制”这一法律问题,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法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这样、马克思便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学观的批判,澄清了法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即法的客观性及其本质。他不再停留在“私人利益决定法”的命题上,而是把握“市民社会决定法”的深刻精神,从而揭示了财产关系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当然,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把市民社会同物质生产直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没有把私有财产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没有弄清现存生产关系与其法律用语“财产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因此,“市民社会决定法”这一命题尚未获得全新的意义。但是,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思想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因为马克思抓住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这一基本原则,就从根本上揭开了一切政治和法律现象的谜底,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奠定了基础。(二)、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样一个在法哲学领域中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并把解决这一关系看作是消除国家与个人之间异化现象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批判地继承近代启蒙运动突出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人的权利的进步精神,尤其是批判地吸收了卢梭的思想,对黑格尔关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统一性的命题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第一次提出了要从现实的人的活动中把握人的本质的思想。这是他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形式和法的关系思想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唯物主义原则在探讨人的本质问题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人的普遍的和客观的特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强调要以 “现实的人”为基础,从“现实的人”的活动中揭示人的“社会特质”,进而与黑格尔抬高国家、贬低个人的观点相反,重视个人的权利问题,突出个人对国家的能动的独立作用,从而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不仅超越了近代启蒙思想家,而且也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三)、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提出“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的思想。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从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出发,为王权歌功颂德。他指出,黑格尔力图把君主说成是真正的“神人”、“绝对理念”的真正化身,说君主是“人格化的主权”和体现出来的国家意识,从而把近代欧洲立宪君主的一切属性都变成了意志的绝对的自我规定。马克思通过对普鲁士专制国家的揭露批判,阐明了黑格尔这种把封建王权看作是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环节的理论,无疑是主张“任性就是王权”、“王权就是任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还进而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出发,把人民主权和君主主权看作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主权概念,批判了黑格尔抬高君主主权、贬低人民主权的观点。他指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9页),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国王的主权却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把民主制作为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实行人民主权的政治形式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本身以外的意义,每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因而民主制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了的人;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君主制中,不是法律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法律而存在,人是法律规定的存在。马克思说:“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可见,马克思把民主制看作是解决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完善的政治形式。(四)、提出解决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冲突的唯一途径是人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思想。针对西方法学发展史上和黑格尔关于立法权与国家制度关系问题上的种种糊涂观念,马克思鲜明地提出了解决二者关系的原则。他指出,国家制度和立法权之间的抵触,只不过是国家制度本身的自相冲突,是国家制度这一概念中的矛盾。他把国家制度看作是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之间斗争的产物,“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协调,所以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势力之间的一种契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6页)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所谓立法权能改变国家制度的观点,指出“立法权并不创立法律,它只揭示和表述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6页);而只有人民才有权决定国家制度,“从而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国家制度如果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进一步提出了通过革命改变国家制度的思想。他说:“诚然,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对于如何解决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马克思认为,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实行人民直接管理社会事务的直接民主制形式,使人民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真正的国家应当是“人民的国家”。(五)、阐述了唯物一元论的法学认识论和法学辩证法。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而且揭露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他精辟地分析道,黑格尔理论上“失足”的原因在于他唯心主义地理解了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从而导致了颠倒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黑格尔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现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为理念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将法哲学变成了应用逻辑学,即用唯心主义方法来处理社会政治问题。他说:“在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在这里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化为乌有,变成抽象的思想。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3页)因此,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黑格尔唯心主义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二元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二元论的批判分析和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清楚地阐明了,只有从现实的存在物出发,分析市民社会本身的发展及其规律,才能获得关于法的真理性认识。在分析批判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法学辩证法的正确之处,指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2页),也就是关于矛盾的思想。马克思将其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挥,并用它来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黑格尔调和对立面斗争的倾向,即用所谓“居间者”、“中介”、“等级要素”等来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他说:“与其说是中介的存在,还不如说是矛盾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2页)马克思把现实的对立面分为两类:同一本质的对立面和本质不同的对立面,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在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